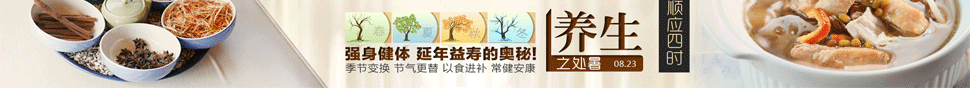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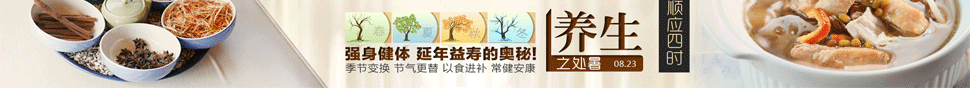
策划高妞制作布衣羊
听
鄢继烈、柳棣、李晋峰、陆鸣朗诵
过年
文/刘汉俊
山里的孩子是盼着过年长大的。
一过冬月,暖和和的太阳就烘得屋檐下的土墙热乎乎的。裹了脚的老婆婆倚了竹藤椅晒着日头,或眯了眼给孙儿挖耳屎,或歪着头给哪家不爱干净的女孩儿捏黄头发里的虱子,还悠悠闲闲地讲些古。老汉儿不时起身回屋,把火炉吊筒上嘟嘟冒气的铜壶往上提一下,再把灶上烟熏的腊鱼腊鸡腊兔肉提出来,晒在屋场的竹杈上,瞟着光亮的膘油,一脸的富足。
远处哪家山包的鼓响了。咚,咚咚,三两声,歇了。半根烟功夫,鼓声又起。近处有人应了。半根烟功夫,莲花塘刘家、月亮湾任家、老屋任家、高井畈刘家、架桥郑家、鸭棚梁家、坡里童家、望山邹家的鼓陆陆续续响起来,遥遥对对,零零密密。畈里人家再穷,砸锅卖铁,不吃不喝也得蒙一面像样儿的单面牛皮鼓。大屋坡小山冲,家户人再少,也少不了鼓和土铳。“走哇,赛鼓去了,今年劲要硕啊———”青壮汉子吆喝着,眼睛瞪着像牛卵子。孩子们前呼后拥,像鸦雀儿泼了蛋。家家户户的鼓排在古柏树下金黄的禾草上,支张老方桌,摆了些酒菜。红衣绿袄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偎了自家菜园门,掩了嘴儿哧哧地乐。爹爹们蹲得远远的,捻着须,眯起眼,点点头,撸撸下巴。不时念叨谁家又出了匹好鼓。那鼓声,一下,两对,三棒,有节有奏,时轻时重,亦稀亦密,一呼一应,有挑有逗,绵里藏针,你追我赶,远里近里,鼓外有音,把个十里八乡炸得像豆子进了热油锅。
落不到打鼓的细伢们,早早放起了鞭炮,一个个拖着尾烟的冲天炮凌空炸裂。偶尔有小串鞭炸响,准是哪家小子实在憋不住,偷放了大人晒在瓦顶上的年鞭。谁家小儿不小心,鞭炸在棉袄里,过年的新衣即刻烧了一圈圈镶黄边的黑窟窿,招来当妈的一顿笤帚追打。
鄂南幕阜山区赤壁的年,在鼓声与鞭声里掀开了帘子。
落雪
过年不能没有雪,尤其是山里。
雪通常在冬月尾开始飘洒。老人们拄着拐杖,伫立在烟黑色的禾场上,望望天,半晌叹道:“该落雪了!”“是,该落雪了。”“噢,呵吼,要落雪了!”孩子们一片欢呼。这雪,就着炊烟,在某个青紫色的夜霭里降临了。
咦,哪这亮?赖在暖被窝里的孩子揉开糊着眼屎的眼,问。“落雪了,”早起的大人不经意地应。“落了,真的?”掖着棉被往格子外看,一阵狂喜,猴急猴急地套上棉裤厚袜,嘭嘭嘭地敲打下堂屋的门:“哎,落雪了!哄你是崽!”三个两个,七个八个,孩子串起来,踏薄雪去了。胆子大一点的,用狗毛领捂了脖子,到风大的屋场踩雪。临了捏上几个大雪团,等着灌女孩儿家的脖颈子。
冷了。大人家翻箱倒柜找铁罐头盒或洋铁筒儿,用锥子穿双对眼,拿铁丝系了。去年冬天捂得的木炭拣出来,在火炉里燃一燃,放进铁筒儿,一个热得炙手的熏火筒儿就成了。上学、串门儿、撒野儿,都提在手上。
大一些的孩子用树杈儿削成枪托,凿一凹槽,比着尺寸锯一段巴掌长的钢管作枪筒,后座敲进一管穿眼的弹壳儿,用洋铁皮扎稳当,再削支一寸见长的撞针,用铁皮蒙紧,嵌进扳机,绷上强力皮筋,一支左轮手枪就成了。茅屋猪圈的墙上,浮有厚霜般的硝,刮了来与炭末等其他药引混着炒,便成了火药。一不过细炒烧了,喷起的赤焰能把人眉发燎了。药灌进枪膛,用铁钎筑紧。装上铁铳子,便有了杀伤力。一角钱8粒的纸火炮贴在撞针前端,一扣扳机,嗵地一声药弹就出了膛。有枪的孩子胆儿壮,撵着背土铳的大人屁股,上大雪封住的山冲捉兔子,少不了要喝上前奔后窜乖巧威猛的看家狗。茅山张家的一个孩子枪走了火,把个正端枪猫腰聚精会神地瞄准的大人屁股打成麻饼,十几粒散子如今还没挑出来。
等到大雪封了山路,除了堆雪人儿、打雪仗、溜雪坡,孩子们已没得好玩的了。太阳一出,各家天井、屋檐下挂起如瀑如线的冰凌,长长短短,粗粗细细,密密疏疏。祖堂屋后背阴处,有惊人的粗长冰柱,招来老老少少的围观。握在掌上,怕化了,捧在怀里,怕摔了。
年饭
雪越落越深。天越来越冷。家家户户的塌炉、熏箱昼夜不熄了。谁家塌炉篾栏上烤的尿布糊了,谁家灶炉角里瓦罐鸡汤沸了,谁家的腊味、鱼糕蒸得香死人了,谁家炒了米泡儿、苕角儿、糖糕儿、豌豆儿,还有酥糖、雪枣、金果儿,惹人流口水了……
年,真的要来了。
扫扫一年没顾上的扬尘,把新连的罩衣、蒙袄给孩子们试试,进城的人捎回点红绿气球、灯笼、对联,年的颜色也有了。
年节之前给亡故的亲人送灯,必不可少。坟就在后山坡,林林密密的青冢、碑井有些阴森、凄凉。一辈子没出过山冲的老人们,魂也守望山垅。油灯有用马灯的,也有纸糊的、烛照的,放在避风处,不管夜风多大雪多密,坟地的灯光一夜不熄,远看若星河迢遥,天街有灯,隐隐约约。除了送灯,有的人家还备些祭食当年饭,再放一挂鞭,算是天上人间两厢牵扯了。
山里的年通常要过个把月,过年的标志是吃年饭。莲花塘刘家的年饭一般是腊月三十正午吃。流水港丁家的年甚至更早一天,腊月二十九的晚上,丁姓人家就开始吃年饭,意思是先吃先有,因此落得个“好吃丁家”的名声。
正午稍过,山坳里吃年饭的鞭炮声响起,密密麻麻、断断续续、催催停停、稀稀落落。约摸半个时辰前后,各家鞭声彼此响应,硝烟未清就关门吃年饭了。
腊肉腊鱼野兔山鸡鱼糕蛋卷藕夹榨鱼苕粉,糯米丸子梭衣丸子米泡丸子肉丸子鱼丸子,煨骨头海带汤湖藕汤炖鸡汤汆元汤汆肉汤银耳汤米粉汤,炒红菜苔白菜苔冬笋香菇包菜红白萝卜青蒜……百色百样。年头吃鱼头,年尾吃鱼尾,木桶蒸饭不得吃完,这叫年年有余,岁岁有剩。叫花子也有三日年,再穷的人家也得像个样,一年的好场合都留在这一顿上。敬老人嘱后人酒来酒去烟去烟来大人劝小儿闹狗啃骨头到处钻,热闹非凡。直喝得天昏地暗,东倒西歪,伢儿认不得娘,老头媳妇找不着茅房。年饭收拾停当,稍事歇息,女人们便忙着命男人小孩褪下旧年脏衣,全家老小洗个热水澡,一年的辛苦和风尘一夜洗尽,留个清清爽爽轻轻快快好过年。
“三十夜的火月半夜的灯”,家家户户三十夜的炉火都烧得噼啪通红,焰高一尺。膛中有火,心里有主,一家人偎着火守着直冒香气的煨蹄膀湖藕汤。大人嘱孩子穿新棉衣的小心火烛,穿新棉鞋的莫踏湿、蓄着点。老人们吧嗒着抽烟,咕噜着茶壶嘴,检点一年的亏盈,盘算来年生计,不时嘱两句儿孙辈做人作文做事之类的要经。剽悍的狗蜷在灶角,偶有火星溅着,汪地一声跑远了。时间钝滞,像火上的汤,就这么熬着。
屋外的雪,戚戚地落。各户的灯火映了,雪光有些带紫。趴在窗棂看远处,厚厚的雪被捂不住星星点点的夜火。
拜年
大年初一清早的鞭炮最烈。这村那家此起彼伏没得间隙,鞭中夹炮,炮后有鞭,一阵紧似一阵,一村密过一村,像滚雷拂过村村畈畈、旮旮旯旯。各家各户起床的第一桩事,是赶紧把鞭炮屑用笤帚拢了和垃圾归在里屋门角,不能泼出去,要留住“财岁”。
早点过后就开始拜跑年。初一初二拜本家,初三初四拜娘家。同姓本家从祖堂屋拜起,上房下房,穷家富家,叔老伯爷家家叩遍。推门而入,双手一拱“恭贺恭贺”,逢年长者需问几声健旺,儿孙辈得趴在地上一磕到底。本家一般不备礼,也不送压岁钱。陈年的情分,积久的恩怨,消融在这两手一拱之间了。有在外头挣工资的回乡拜年来了,自然要阔气一些,主人家也想多留两脚,问问在哪里发财,恭贺恭贺,羡慕羡慕,一团和气。本村和邻村的拜跑年,有时需一天方能拜完,相好的聚在一起,喝两口,有些过结的难免有些尴尬,但年上图个吉庆,不说隔墙话。
不管是风雪连天,还是冰释雪融,山山相连、村村相通的山道上总是穿行着花花绿绿打打闹闹拜年的人。年年如此,家家这般。父亲因读了大学又教大学,是有身份地位的人,在老家远近闻名。每到一处拜年,父亲喊舅、叔、娘的都数不过来,老人们慈爱地唤着他的小名,揭他我们从没听过的老底儿,这时父亲总是很兴奋、恭顺得像个孩子,被数落得不好意思了只好冲我们呵呵一笑。家家都以父亲的来访为荣,三家来约,四家来扯,家家都得吃席。
隔壁左右的兄弟伙伴儿来了,得炖着热漉漉的炭火锅随意喝几盅。但至亲至戚、同庚旧友、结拜兄弟、生死之交来了,真正的拜年饭就很讲究。通常是酒席的主桌摆在上堂屋,桌缝与堂屋横梁平行,长者和主客背墙面门坐上席,一览重重下堂屋;次位是下席,与上席对面;两侧是边席,多是晚辈等陪客,专侍筛酒的须是辈分最小的男丁,坐边席靠近上席的位置。两侧偏桌一边是半大的小伙子,一边是有点见识和开达的女人加上哭闹的孩子。媳妇和大姑娘们一般不上桌,须客人全吃完后再端着饭碗挑些喜欢的冬笋、粉条之类的剩菜。主菜惯例是八大碗,用碗倒扣的肯定是腊肉了,但一般是肥多瘦少,有的壮劳力一气能吃七八块一咬一口油的大块肥腊肉。酒有打来的散酒,也有家酿的,灌进壶,淤在炉灰里温一温。话题有时热闹得不可开交,有时又东扯西拉同不了题,就这么默默地干坐,却也那么自然、舒坦、妥帖。边吃边喝边聊,主人忙不迭地夹菜,主人家媳妇不时上来站在上席旁边用油乎乎的围兜拭手,边邀着:“您家吃,随便夹点什么,没得好菜,得罪您家了。”在上堂屋吃喝上家的酒席,下一家的主人早手持酒壶一边候着。上家吃罢,酒、菜全撤,碟、盅、筷不动,人也基本不动,只是筛酒人换成下家晚辈。热气腾腾的酒菜从下一家灶屋里端出来,绕过天井、侧廊和堂屋就上了桌,品种花色差不多,酒味也差不多。吃第二席时,第三家也早立在边上了。七家八家十家,从晌午吃到天擦黑,按辈分长幼来排队,少一家都不行,否则就是嫌贫爱富瞧不起人。到最后,只能一家只动几筷子,抿一口酒算是表示了。这昏天黑地的一天,是亲情最浓郁香醇的日子,整个山冲,弥漫着安宁、静谧、祥和的氛围。
龙灯鼓阵
正月初三,大姓屋场的龙灯就舞起来。最先是一个姓舞一条或几条龙,后发展到同村组、同一个生产队舞。男男女女青壮劳力全出动,人少的舞两条,多的舞四条,公龙母龙成双配对。牵珠的须是身手矫健的壮小伙,与其说“二龙戏珠”,莫如说“珠戏二龙”,带响铃的彩珠上下挥舞,撩得偌大的龙身上下翻飞左腾右扑。龙后面往往跟有采莲船儿,俊俏媳妇涂脂抹粉地立在采莲船中央,扮相滑稽轻佻的艄公执篙在前面逗引,男扮女装佯作愠怒的艄婆操起破扇子在后面追赶。在谁家堂前停下,立即围成里外三层。艄公唱:“采莲船呀么———”,众人齐唱“哟呵”,“拜新年呀么———”,众声紧接“划———着!”……各家各户赶紧放鞭来接,再往采莲船头搭上些烟、糕点、布头之类回敬。阵容大一点还有狮子和花鼓戏来伴,两个年轻人钻进狮身,大摇大摆,爬桌椅、钻长凳,博得一阵阵掌声喝采,也有调皮的狮子专追赶大红大绿的大姑娘,吓得她们呀呀怪叫,小儿们直喊“妈妈”。
真正壮观的场面,是鼓阵。黑夜的山道田埂上,一队队的各色花灯在前引路,向某处村庄进发。鼓阵紧随,几十面、上百面牛皮鼓一齐发作,几十里外就能听到,人们凭鼓声判断有龙队去哪个方向了。出发后,鼓点节奏完全一致,齐响齐停,这叫排鼓。排鼓雄宏壮观,整齐划一,富有震撼力、凝聚力。鼓的一头,用土铳、梭镖支着。两个家族之间的龙是不能碰头堵路的,否则将发生火并,双方都要设法将对方的龙皮划破、龙须割断。浩浩荡荡上百人的队伍临到某个村落路口,排鼓顷刻间变成乱鼓,算是报信。花灯队先进村,到得主堂屋下齐刷刷站定,待主人出来,鼓阵在村外立住,乱鼓不停,长龙、彩狮、采莲船依次徘徊游弋。村里接客的鞭炮一响,鼓阵就开始前行了。蓄了一冬的汉子们,把力气都用在了鼓点上,威风凛凛地从村里穿过,在村的另一头候着龙队。少了花灯龙队的鼓阵出不了彩,缺了鼓阵的花灯龙队没有了威风,你来我往的龙灯鼓阵要闹到正月十五花灯节才能歇手。
多少年了,过年的感觉依然停留在儿时的记忆中。城里的年过得虚浮、喧闹、忙碌,少了些实在、浓稔、醇香,那不能算过年。乡亲们年年捎信让我回家,我也一直向往,何日再回一别多年的故乡,过一个真正的年?
我们给大家拜年啦
祝大家:,一顺百顺!
SPRINGFESTIVAL
作者
刘汉俊
湖北赤壁人。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主任、中宣部"学习强国"总编辑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朗诵
鄢继烈
国家一级演员、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、中宣部“学习强国”播音朗诵专家团队成员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奖”获得者、国家語言.文字先进工作者。
柳棣
原名柳小平,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,中宣部“学习强国”播音朗诵专家团队成员,湖北广播电视台播音指导。
李晋峰
国家一级演员、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、中宣部“学习强国”播音朗诵专家团队成员。
陆鸣
国家一级演员,中国曲协理事,湖北省文联副主席,省曲协主席;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,曾获“中国首届相声节金玫瑰表演奖”。
记录声影传播温情
布衣羊的声像
布衣羊
声明
本作品中的文字、图片、音乐、演唱、影像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朗诵音频由“布衣羊的声像”制作合成,如果转发请注明来源。
第期
原创编制:布衣羊的声像
投稿邮箱:
qq.
